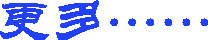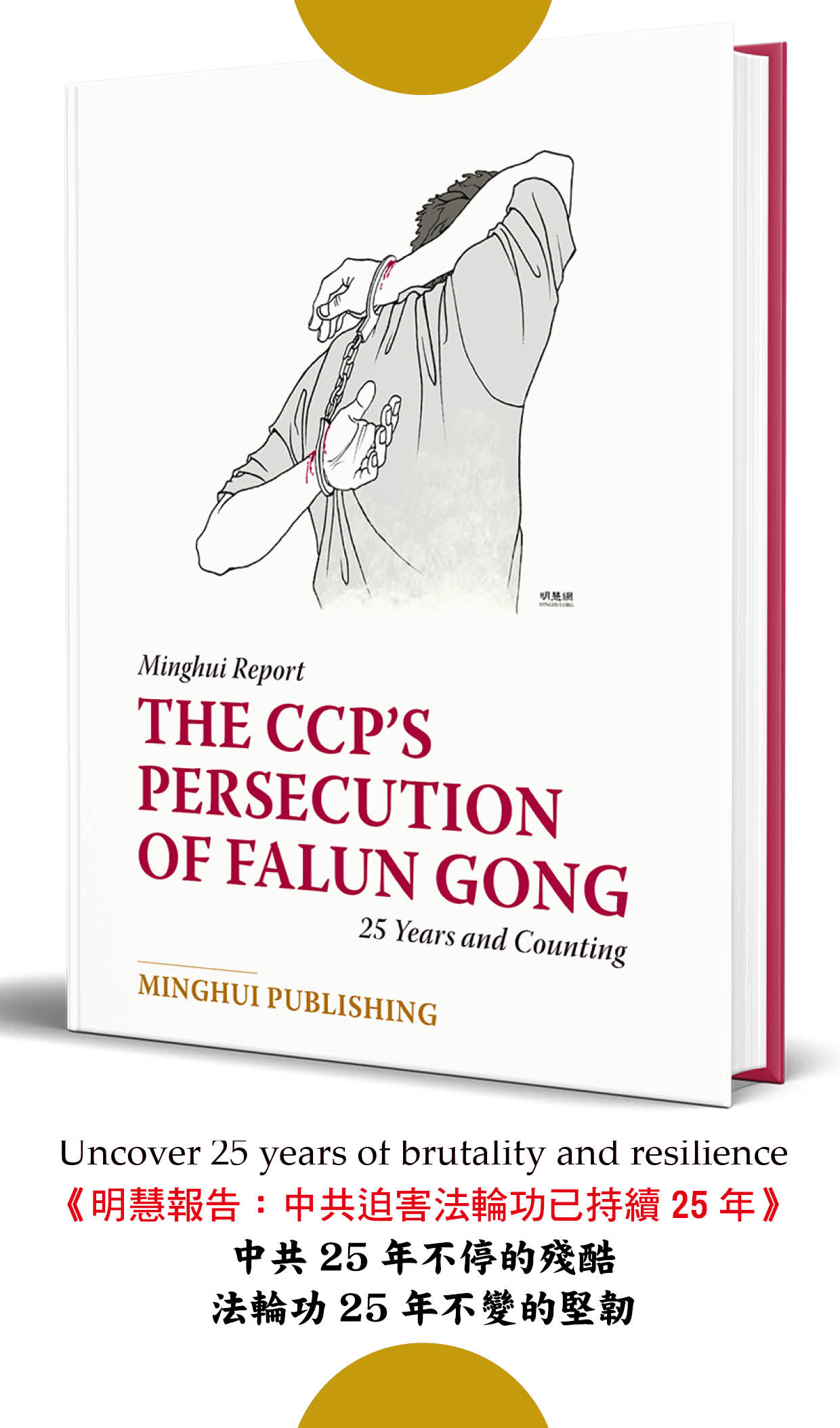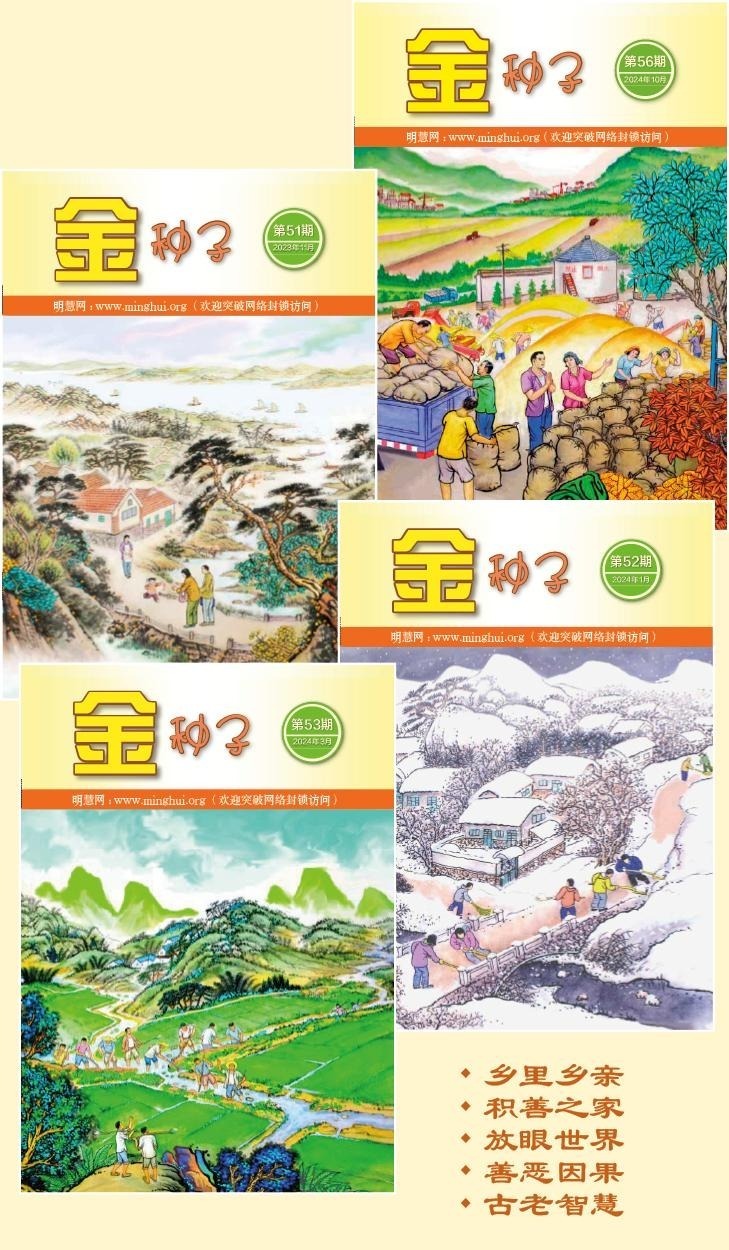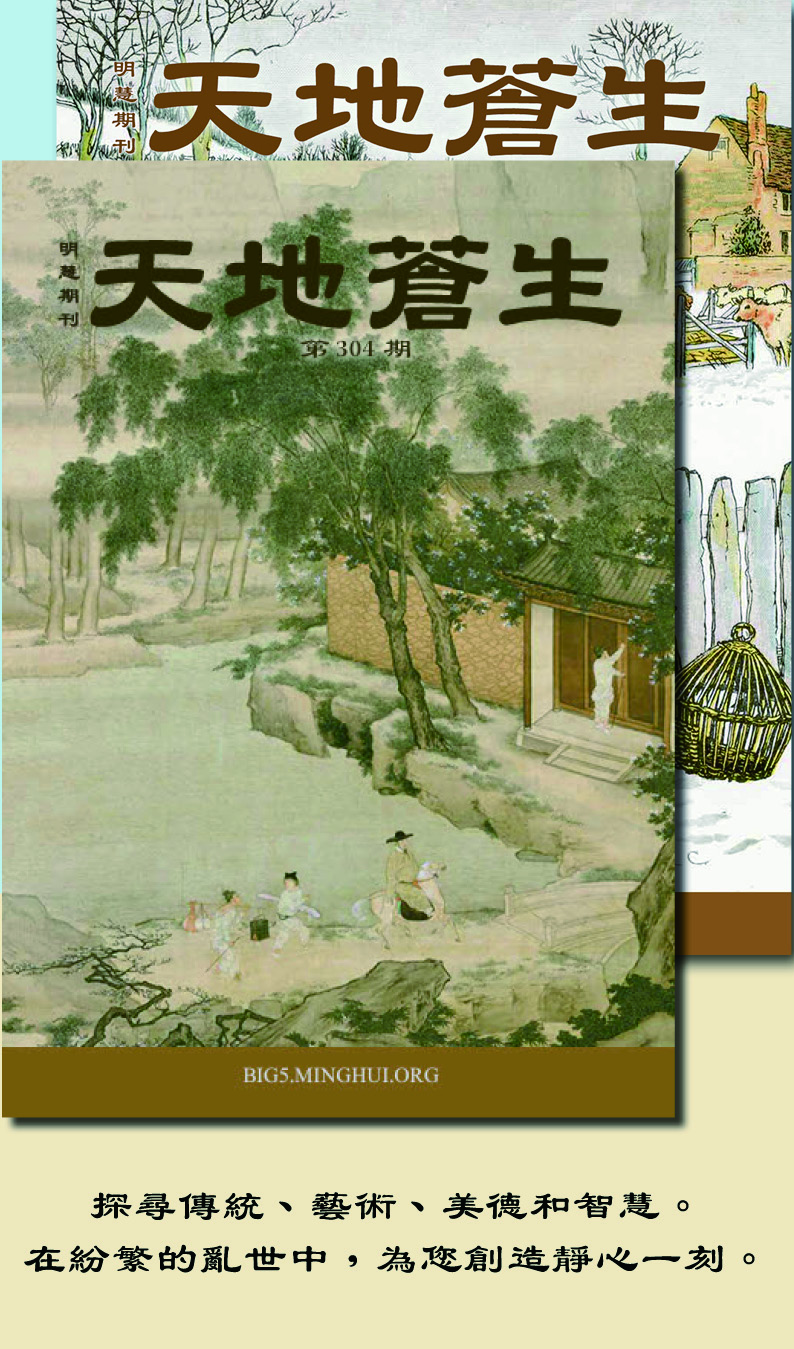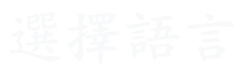【大陸法會】沒甚麼可怕的(上)
——一切是我們師父說了算
| ──摘自本文 |
慈悲的師父好!
同修們好!
我是一九九六年五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七十三歲。在二十九年的修煉中,是慈悲的師父時時看護著弟子,加持弟子闖過了一道道險關,履行著自己助師正法、救度眾生的神聖使命。下面將自己的一些修煉經歷向師父彙報,與同修交流,更希望通過自己的經歷給害怕迫害的同修一點借鑑與啟發,早日去除怕心,共同完成大法弟子的神聖使命,做讓師父放心的大法弟子。
一、師父救了我好幾次命
多年前的一天,我在大商場附近講真相,遇到一位小伙子,他聽我講完後說:「我就想找個貴人哪。」原來,他宿命通功能開著呢,知道人類要有大災難,嚇的不得了,就想找個貴人救他。我說:「那我今天就是你貴人。」我就跟他講,有大災難時只有大法能救他,他很接受,他說:「大姐,你從那一路過,身上都是金光閃閃的佛光啊。其實你師父都救你好幾次的命了。」我說:「小時候我總是死了活了、死了又活了的,那是我師父救的啊?」他說:「是啊,就是你師父救的。」
我出生以後就天天生病,我媽說我得一個叫大肚皮的病,臉焦黃的,精瘦的,成天往醫院扛我,死過去一回又一回的。因為花錢看病,折磨的我父母吃不上、穿不上的,都沒錢過年。有兩次最嚴重的,一次都把我放地上了,裹屍的草都準備好了,就等著人沒氣後扔了。那時扔死孩子只掙一塊錢,有個人為掙那一塊錢,總問我媽我啥時候去。那時也看大仙,看看我,能動了,又好了。第二次,眼看又要死了,父母抱著我去縣裏一個挺有名的醫生那看病,醫生看到我後驚訝的說:「哎呦,這孩子都這樣了,咋才來呀?這孩子可夠嗆了。這麼著吧,死馬當活馬治,照肚子扎一針,給你包點藥面回去吃,見到耳朵有血筋,就來一趟,沒這種情況就別來了。」吃完藥面後,真見到耳朵有血筋了,就又去了一趟,我就好了。
我三姨和我說:你小時候老折磨你媽,常年有病,把家都折騰窮了,都穿不上衣服了,穿包裹皮,過年都吃不上肉。三姨總告訴我:「你長大你可得孝敬你媽呀!要不你對不起呀!」我有時想,我家人身體都挺好的,咋就我這樣哪?我媽在吃上都照顧我,我這個不吃,那個不吃,一九六二年困難時候,人家都吃薯秧子啥的,我媽都得給我弄點小米,因為我身體不好。
我二十歲左右上廠裏上班,又得了血崩的毛病,經常月經大流血。有一次血紅蛋白指標都剩兩克半了,正常應該是十一到十五克,少於十克就是貧血,我差點又死了。輸了一千四百毫升血,輸了十多個人的血。因為大流血,我把縣裏的醫院都住遍了。等我好了後,醫生說:「那時我都不敢看,看到你的時候,(嚇得)我的腿肚子向後轉,沒想到你還活了。」
從小到大,我的身體就一直不太好,連死帶活的,人也長的又瘦又小。修煉後才知道,是慈悲的師父早就看護著弟子,救弟子的命,才有了我的今天。
二、幸得大法
我因為身體不好,也沒少學氣功,都沒管用。後來我同事告訴我:大法好,學大法能成神。我還開玩笑的說:「哎呦,我還能修成神,還能上天。」雖然這樣說著,我也去煉,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一邊看大法書,一邊看師父講法錄像,我特別愛聽師父講法,覺的這個大法這麼好啊!那時就是一個高興啊,剛得法那種愉快的心情無以言表。
我每天早晨去附近的一所大學校園煉功點煉功,有兩個男大學生教功。校園裏開著花,環境很好,我的心情也特別好。後來學法的人越來越多,我們廠區也有了煉功點。同修們早晨在一起煉功,見面時,總有人說起自己受益的神奇事。
我一開始修煉大法,就覺的和以前學的氣功不一樣,我愛聽愛學,師父也給我往外推病業。我以前怎麼鬧病也不發燒,單位醫院有個規定,不發燒不給開病假條,我雖然病的特別難受,因為不發燒也開不來病假條。我剛一煉功就發燒了,頭一次知道發燒的滋味,連骨頭都是疼的。當時我重視學法,悟性還行,我想這是師父給我往外推病業,是好事。結果很快就好了。那時我還噁心,說噁心就吐,但不影響吃飯,說好就好。半年後,我的身體達到無病一身輕。
我高興的到處講大法的美好。我們廠區有個同事,煉功後發燒了,他說自己煉功前不發燒,這怎麼還發燒了?不學了,與大法失之交臂。很可惜。現在看見他,我說:「大哥,你看我煉功身體多好!」有個同事開玩笑的說:「你看你,工廠花錢的時候你得病,現在自個花錢了,你沒病了。」我笑著說:「哥呀,是,工廠花錢時我長病,現在我為啥好了?我學大法學好的。我要不學大法,我早死了。你也學呀,你學大法,你也好。」
三、進京護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惡迫害開始後,陸續有大法弟子進京護法,聽到同修們一件件放下生死、可歌可泣的壯舉,令邪惡膽寒,我為同修們高興、感動,師父的弟子真了不起呀!我們大法弟子都應該進京護法,助師世間行。我悟到了,可不敢去,我很著急,吃不好,睡不好,著急的直哭,就覺的對不起我們的師父。
我的家庭情況,當時就覺的沒我就不行似的,把家放在第一位。我想這不行啊,這麼好的師父,這麼好的大法,師父受冤枉了,大法被誣陷,因為小家影響大法弟子助師世間行,這不行!進京護法這是我一件最榮幸的事,還有甚麼比這重要哪?我就琢磨著哪天去。那時家裏不是我管錢,我就攢點錢。
除了家庭,我哥也是我的一個壓力,因為我一個哥是廠領導。廠裏說:有親屬煉法輪功,要是上北京,就撤職。家人都說:你可別去呀,去的話,你哥那幹部就得撤職了。我面對選擇,還是決定去,還是師父重要,法重要,我必須得去。
二零零零年大年三十早上,我約了一位同修一起去。一走出家門,我就高興的哭了,覺的自己能為師父、為大法說句公道話,能了了一樁心願。到火車站,還遇到其他同修,上了火車,心情很複雜,因為當時形勢很恐怖,上車還檢查。但弟子們心正,師父保護,我們一路順利到了北京。
下火車還碰到附近縣的同修。路過天安門時,就看到有一對從農村來的夫妻同修被綁架了。大過年的幹啥來了,就知道是法輪功學員。因為我怕冷,穿了個舊棉襖,像農村來的,我也挺擔心的,害怕歸害怕,能來證實法那心情是喜悅的。其他同修幫聯繫,到晚上給我們找好了住處。那時又累又冷,我還發燒,可算到了地方,歇一歇。可過了一會兒,有同修說這裏不安全,還得走。上公交車會被查,就是步行,或坐小三碼車。我們又冷又累,要是為其他事就支持不住了,因為做的是最神聖的事,多痛苦也堅持。大年三十的半夜三更,我們走在北京附近的小道上,真是「百苦一齊降」(《洪吟》〈苦其心志〉),但一想到師父,心裏就暖呼呼,非常高興。
到一個地方後,沒躺多會兒就到早上了,又起來,準備去天安門。有自發協調的同修看有的同修沒有橫幅,把我的橫幅給同修了,讓我負責發傳單,發傳單比打橫幅要危險。我想讓我幹啥就幹啥,為別人著想。這次是坐車去,心裏有點害怕,但我知道害怕也得做。在到天安門前一個人群最多的站,我們下了車,那是早晨上班時間,人特別多,同修們就開始打橫幅,喊:「法輪大法好!」我在高處拿著傳單,對著人群一散發,發時很神奇,傳單到處都是,警察過來撿傳單,沒來得及顧我,我就脫身了。打橫幅的同修被警察綁架了。我想天安門還有大法弟子,還接著做,自己就步行去天安門,一心就想證實法,做好這件事。
在那種恐怖的環境下,天安門廣場到處是大法弟子,這一片打橫幅高呼:「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我師父清白!」那一片又開始打橫幅高呼:「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我師父清白!」那聲音響徹雲霄,響徹寰宇,那種震撼,用盡人類的語言也無法形容,我感動的直哭。有大法弟子打橫幅,我就過去一起打,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我師父清白!」那時大法弟子不管認識不認識,特別有凝聚力,整體配合的特別好。不認識的幾位山東大法弟子要打一條好幾米長的特別大的橫幅,我趕快過去幫著拽,想趕快打開。我能幹啥就幹啥,直到被警察綁架。
大年三十去北京的同修特別多,天安門廣場到處都是便衣警察,被綁架的同修被一輛接一輛的大客車從天安門拉走,滿載著大法弟子的大客車數不過來,那場面太悲壯了。在車上有同修給警察講真相,講到有開天目的同修看到師父在和外國人講話;看到師父在天安門廣場上方看著大法弟子;有拉大法弟子的車走走就壞了;還講師父的故事,說師父生活簡樸,給孩子買兩元錢的鞋,不買貴的,警察都默默的聽著,不反駁。
後來聽說抓捕到半夜十二點就不抓了,因為沒地方擱人了。我們被拉到一個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同修,大家一起背《論語》、背《洪吟》,喊大法好。因為警察要把同修分開帶走,同修們就胳膊挽著胳膊,腰抱著腰,不讓警察把同修單獨帶走,因為人特別多,警察踏著我們後背上,給照相,識別人。我這一路都被同修們的正念正行震撼,感動的眼淚不斷。
後來我和很多同修被拉到一個收容所,在裏面晚上沒有被子,後來給個破被子,又被拽走了,還開著門,開著窗戶,把窗戶潑上水凍上。大家早晨背法,喊大法好,講真相。時間長了,這樣背法他們也不讓,派來一個排的武警,把大法弟子拽開,不讓大法弟子在一起。幾天以後,有的報名回家,有的被整走了。還問這個活動(背法等)誰組織的?沒人吱聲,有個小姑娘說「我」,他們就把小姑娘帶走了。最初人挨人的屋子,後來人越來越少,剩五、六個人了,我們不報姓名,不報地址。後聽說家裏到處找我,到派出所找我,查我的名字。幾天後,我和同修被帶回本地。
我曾聽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我永遠不能忘。說有大法弟子被抓進去迫害,在魔難中受不了了,說不煉了,走出監獄大門時,看見我們的師父了,我們師父為我們著急,眼睛裏流出來的都是血呀。這個大法弟子看到後又回到監獄裏。我聽到這件事,心特別難過,師父為大法弟子過不去關著急啊。我一做不好的時候,我就覺的對不起師父。在救眾生上,師父那麼著急。看師父《對澳洲學員講法》錄像,我就哭,師父為了救眾生,操盡了苦心。大法弟子做不好,師父著急。我就想,必須做好,回報師父,讓師父放心。
從迫害開始,我就開始講真相。那時候還上班,我在車間講,走到哪講到哪。那時環境也很惡劣,公安局的下來查,單位逼,家庭逼,再加上我哥那,壓力挺大,但我就是堅持講真相。有的同修說自己還沒修好呢,還護法。我說:「這就不對了,護法還等著修好嗎?等你修好,這個階段過去了。沒修好,咱們慢慢修。師父被陷害,大法被侮辱,大法弟子進京護法,有這個責任,咱們沒修好,咱們修,這階段不能錯過,就應該去。」那時心性也不高,跟同修說也帶著氣,心想這麼大的事還等修好再去?
第一次從北京回來,公安局、派出所的人讓我們寫保證不進京,還押三千塊錢,說誰第二次去,這三千塊錢就不給了。有沒去的就領回了。我又一次去北京護法,錢就沒領回來。我想:我去北京不比領三千塊錢高興啊。
市裏要辦洗腦班,不寫不煉功保證的送洗腦班。我就寫了。交上去後,他們說:你這叫寫保證?你這是寫決心呢。我說:這麼好的大法,寫甚麼保證啊。這樣我就被綁架到洗腦班。那是市區挺偏僻的空房子,有警察、有各個單位派去的人,晚上睡覺還有警察在走廊站崗。我丈夫這次表現挺好,他去找我,說也沒事,從單位把我給帶走了。同修們在裏面做好事,打掃衛生,有啥活就幹,還給他們講真相,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得救了,把洗腦班的頭兒感動了,說:「大法好,你們要努力,好好學,好好煉。」
四、守住正念,就按師父說的做
剛開始沒有真相資料,我就手寫去貼,用漿糊貼。A4紙裁兩半,白紙紅字正體,總寫,寫的還挺漂亮的。民工在那修馬路,我和同修貼的到處都是,一路能講就講,能貼就貼。有時有伴,有時沒伴。有一次,我去一條主幹道去貼,那裏過往的人多,我想早點去貼,人少點。我正貼呢,土坡那邊有個男的「嗷」的一聲,我跑,他就在後面追,跑了很遠,跑到一個小樹林子裏,我實在跑不動了,他追上我說:「你跑啥呀?」我說:「你追我幹啥呀?」他不是想抓我,是個色鬼。他沒敢動我。跑的我嘴釀白沫子,等我走回家,一天嘴裏都有白沫子。
二零零八年要開奧運,體育館旁邊都是警察。有一次我在那附近講真相,旁邊有幹活的,有個小伙子,表現特別好,我跟他講,他也退了,我接著勸別人的時候,他還幫著我勸。他穿過馬路走時還朝我樂呢,卻是到警察那報警去了。我剛要走,警察到我跟前了,把我綁架到附近的派出所。我平時看《明慧週刊》很仔細,不管是病業關還是被迫害的交流,還是其它方面,做的特別好的我都多看幾遍,腦子裏都能記住。我被抓後,想起同修在被迫害時是怎麼樣能闖出來,怎麼樣能證實大法,我就借鑑一下。我就講真相,見到警察講,見到一般人也講。沒人時我就坐在那發正念,來人了我就講。警察說:「你看看她你看看她,她一會兒也不閒著。」
他們讓我呆的房間中用鐵皮擱開一個地方,他們在外邊說啥我能聽見,我就到外邊和他們接話。他們說:「太累了,成天讓巡邏,累呀。」我就說:「你們知道吧,這都是邪黨幹的,這江大蛤蟆要是把社會領導好了的話,咱社會安寧的話,還用你去巡邏嗎?是不是?咱們多好啊,安安定定的,你們也不用這麼累了,這不就是壞人多嗎,就讓你們巡邏去,這都是邪黨幹的,它不幹好事啊。給咱人民折磨的。」他喊:「住嘴!」我說:「你們不知道啊,我要不說你們知道嗎?是不是這麼回事啊。你們不知道,告訴你們,你們就知道咋回事了。」他們再來人,我還接話,講邪黨惡,講真相。一個女警說:「你看她多膽大,她敢說共產黨。」我說:「哎,共產黨做那些惡事就不能說?誰作惡,咱都得琢磨琢磨,它作惡就不說了?不說你們不明白呀,誰好誰壞,你們要分清,善惡要分明。」他們一看,就不想讓我在這呆了,往外拽我。我就不走,把我襖袖子拽開了,把我放到一個沒人的屋,我就喊:「你們不要這樣做,對你們自己不好,我們師父就是在救人,救度眾生哪,你們得知道大法好,念大法好,保平安。我們師父不看你們過往之過,不管你們在歷史上做過甚麼錯事,我師父都不看,就看你們現在對大法的態度。我們師父就救你。」我不會講,沒把人家講咋樣,倒給我自己感動哭了,我在那哭,一邊講一邊哭。
他們整不了我,把我們街道、社區的人找來好幾個,勸我來了。我說:「你們來了,我沒做壞事啊,我是好人,他們把我抓這裏來了。」我就開始給他們講真相。他們看不行,也走了。晚上十來點鐘,警察把我送看守所。他們折騰了半天才把我送進去。到看守所裏我還是講。符合法的時候,師父都看護著。看守所沒事就把派出所警察叫去,沒事就叫去,給他們煩的。過了幾天,就把我放出來了,是讓派出所給我接回來的。
在裏面時我和犯人說:「不一定哪會兒我就得走。」犯人說:「你咋那能耐啊,拘留你,還想幾天就走。」我說:「用不了幾天我就出去了。」真的沒過幾天我就回家了。在我走之前,又有一位大法弟子被關進來,她狀態不是太好,我說:「別害怕,咱有師父,一定在法上,堂堂正正的闖出去。沒事就背法,講真相,發正念。咱們得做好,讓師父放心,讓師父高興。師父在救咱們。別走人道。」她答應了。等我走時,她的狀態還是挺好的。我走的時候,犯人們說:「她還沒到時間呢,真走了。」
這次和警察打交道,這個派出所的警察都認識我了,在路上碰到都跟我說話。有一次在家附近,跟一位大學生講真相,講完忘給他小冊子了,我就追大學生,沒追上大學生,認識我的警察追上我了。警察開著車,問我:「你幹啥呢?」我說:「救人哪。」他重複一句:「救人哪。」我說:「那可不,就是救人呢。你幹啥去?」他說他幹啥幹啥去。我說:「小伙子,碰上大姨了,得救啊,大姨給你退黨團隊保平安。」我給他起個名字小亮,我說:「退出來啊,咱就得救了,大法就是佛法,誰聽誰得救,誰聽誰平安。不聽就淘汰了。」他同意了,說:「注意安全啊。」開車走了。
這個派出所裏警察大多都認同真相,就一兩個警察不接受真相,半路看見我也不跟我說話,不看我。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拿著漿糊,邊講邊貼真相。有人告密了,警車到我們跟前「嘎」一聲停住了,警察下來一看,說:「又是她。」問:「你幹啥哪?」我說:「救人呢。」他們先搜了同修的兜,有幾本小冊子。我說:「那都是我的,與她沒關係,別跟她說,你跟我說,我就讓她陪著我溜達哪。」正這麼說著呢,他倆把同修推上車了。我說:「哎,咋把她推上車了!」他倆在我和同修之間擋著,我忘了滿手還是大漿糊呢,一手拽一個警察,「啪」一甩,把他倆還甩的挺遠──這不是神通嗎?
警察過來說:「哎呀媽呀,我咋一身大漿糊?」我樂著說:「你看你,別動我呀,我手上漿糊都讓你抹去了。」我就把同修從車裏拽出來了,我說:「沒你的事,你回家。」我和警察說:「沒她的事,小冊子是我的,你讓她回家,有事你就跟我說。」他們知道我那股不怕也不配合的勁。其實是我按法做,為同修著想,一切為他,我來承擔。同修走時挺不好意思的,想回頭和我一起走,我說:「沒你的事。」我和警察說:「有事你就跟我說吧。這是我的。」他們說:「你走吧。我們拉你回家。」我說:「我不想讓你拉我回家,我想自個走。」他說:「那你走吧。」我知道的是弟子按法做,師父救了弟子。
我覺的比起做的好的同修我差很遠,我只是想告訴同修們,面對迫害沒甚麼可怕的,真的被迫害,那就反迫害,就按師父說的做:一是不配合邪惡。師父在經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訴弟子:「作為一名大法弟子,為甚麼在承受迫害時怕邪惡之徒呢?關鍵是有執著心,否則就不要消極承受,時刻用正念正視惡人。無論在任何環境都不要配合邪惡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這樣做,環境就不是這樣了。」二就是在那就是做好三件事。講真相救人,發正念,背法,就做三件事。
每當發生迫害,我就按師父這句法去做「無論在任何環境都不要配合邪惡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再就是借鑑明慧網上同修們的反迫害經驗。同修是師父的弟子,我也是師父的弟子,同修能做到,我也能做到。「怕」得修去,啥也不敢修啥呢?
(待續,明慧網第二十二屆中國大陸法會來稿選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