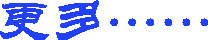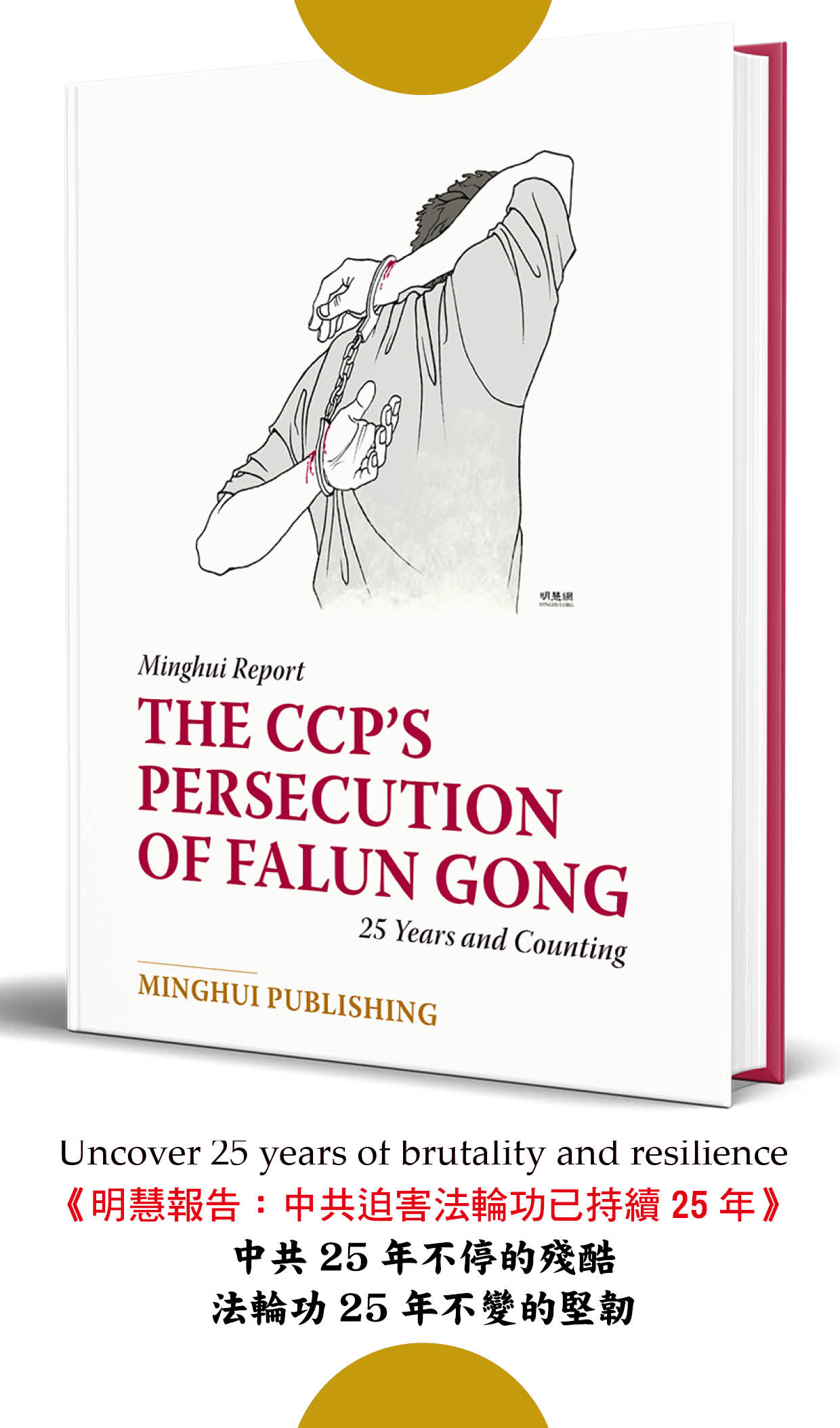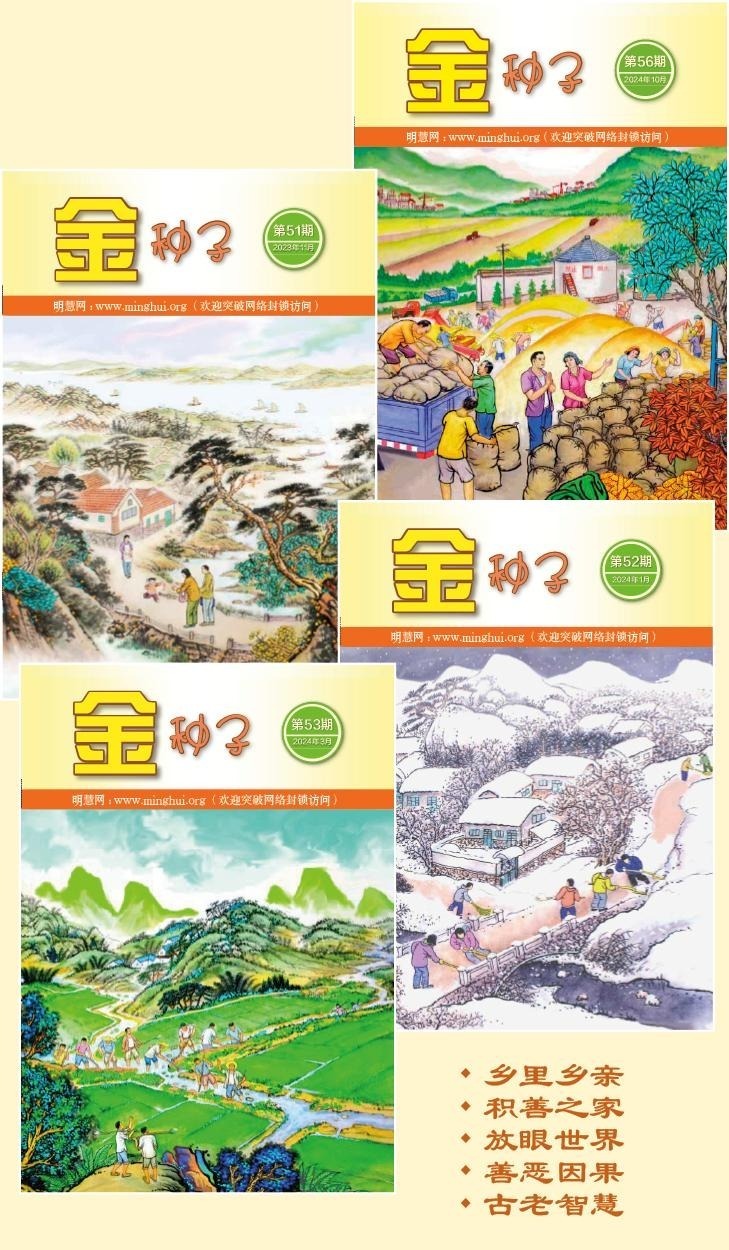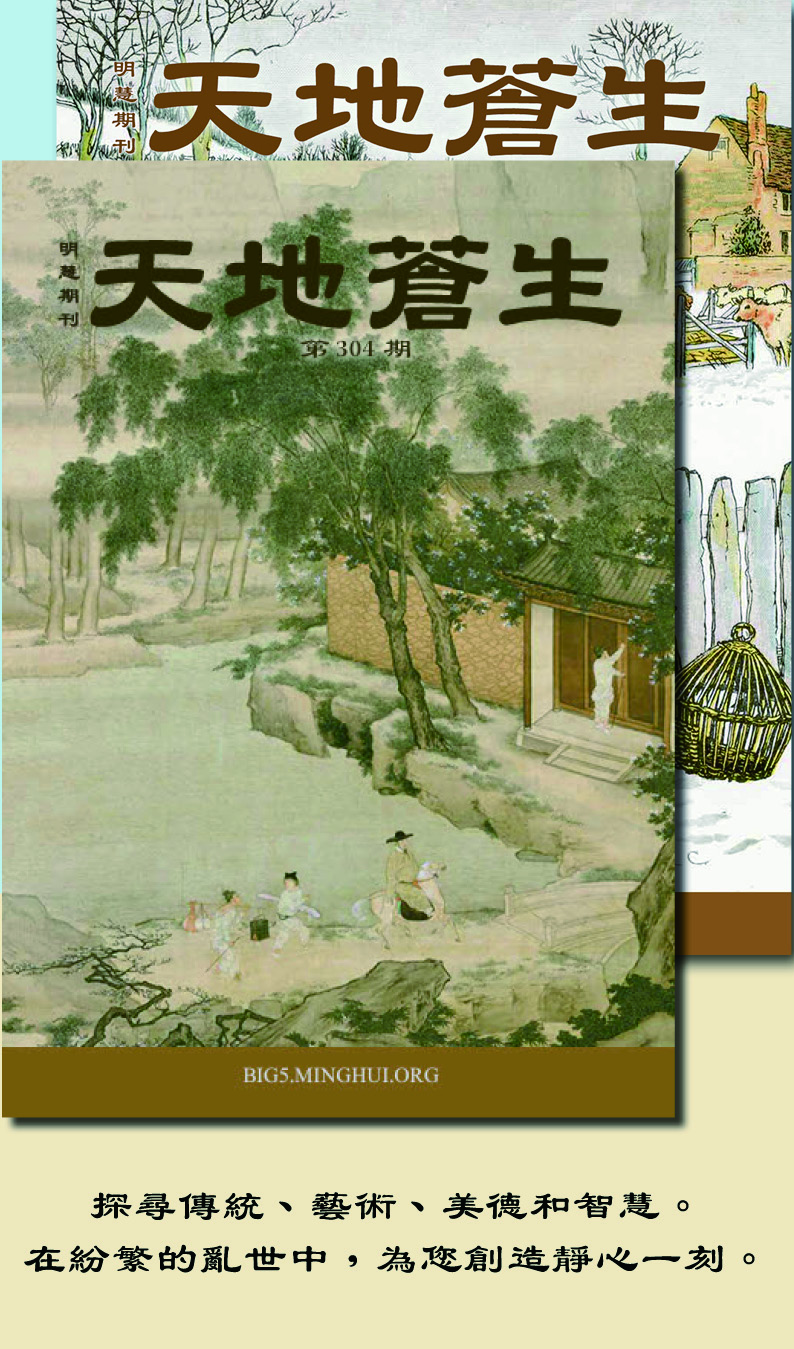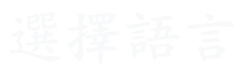【大陸法會】用法律反迫害(下)
做家屬辯護人
我結束冤獄回家後不久,妻子就和另一位同修因在集市上講真相被非法抓捕了。期間,我按照法律程序向各部門投遞了大量規範性的法律文書,將真相內容和法律條文很好的溶合在一起,入情入理,有理有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妻子被非法開庭前,我帶好各種資料到法院申請做家屬辯護人。因為準備周到,當時就通過了。能見到主管法官,機會難得,於是我就以請教的態度,自然的談起了我對案子的看法,請他評判。我從法輪功到底是怎麼回事,到一九九九年為甚麼會發生迫害性的變化;從法輪功學員到底在幹甚麼,到「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這一罪名的適用性錯誤;從犯罪的基本特徵,到「法無明文不為罪」;從歷次的「群眾運動」,一直講到目前利用法律迫害無辜的善良群眾。法官靜靜的聽著,不住的點頭。
這時,從右後方傳來一個女性的聲音:「大哥,你是幹甚麼工作的?說的真好!」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女法官。而且這時我才發現,這是一個大辦公室,好幾個法官都在這裏辦公。
我雖然成為了家屬辯護人,但主審法官告訴我:「上邊有規定,部份卷宗只能看,不讓拍照。」我要求他出示法律依據,他無奈的說:「沒有。」
我找到了法院的紀檢部門,接待我的是一個自稱當過刑庭法官的人。一開始他答應,一定要讓我正常複製卷宗;後來一聽說是關於(構陷)法輪功的案子,馬上翻了臉。說:「法輪功的案子是特殊情況,就是不讓拍照!」我說:「法律依據是甚麼?」他又喊:「這是政治問題,不按照一般法律規定。」同時像情緒失控了一樣,大喊大叫的扯了很多不著邊際的東西。我一邊發正念清除他背後的邪惡因素,同時威嚴的盯著他,大聲告訴他:「不管是甚麼,不能拿嘴說,得拿出規定!」他冷靜下來,說:「我知道你是學者,我不跟你談理論,反正這個事兒就是這樣,我也沒辦法。」
我雖然為妻子請了維權律師做辯護,但在法院問我要不要援助律師時,我仍是毫不猶豫的回答「要」。因為我要藉此向律師講真相,救律師,讓律師在這件事情上發揮好的作用,同時也為律師自己積功德。我很快與一位馬姓律師取得了聯繫,她坦率的告訴我:「我接觸過(構陷)法輪功的案子,也知道法輪功學員是無罪的,但我不敢直接當庭這樣說。」我說:「那你看可不可以這樣?我家還專門請了無罪辯護律師,由他來主導,你隨著他說,關鍵的地方你只要說同意他的意見就行。」她點頭同意了。
這樣一來,我妻子就有了三個辯護人。按規定,每個當事人最多只能有兩個辯護人。我心沒動,心想:如果法官真的提出來,我寧可讓出辯護人的名額,也要成全馬律師,因為那是在救她。結果非法開庭那天,法官完全沒提這事,可能是另一個被迫害的同修沒有辯護人吧。過程中,我們三個辯護人配合的很好,辯護的主體由維權律師來說,涉及敏感的可能觸動邪惡的地方就由我來說,然後就由馬律師說:「我同意二位辯護人的意見。」
再次營救妻子
幾年後,妻子再次被綁架,而且她被抓時,我也面臨流離失所。在需要做出選擇的時候,我在心裏跟自己說:「如果我流離失所,怎麼去營救妻子?如果我流離失所,怎麼結束這個迫害?」於是我決定去派出所要鑰匙,堂堂正正的回家!
路上,各種與怕心有關的念頭不斷的翻湧:「警察會不會正在找我,正等著抓我呢?」我想到了師父的講法。最後牙一咬,心一橫,豁出去了,我就要直接否定迫害,我把自己交給師父了!
到了派出所,我說明來意:「我要回家,但身上沒有鑰匙。聽說我媳婦被你們抓來了,我想知道為甚麼抓她?同時把她的鑰匙給我,要不我進不了家門。」值班警察告訴我,辦案警察一個小時後回來,回來後才能給我鑰匙,讓我先在門口等著。
兩、三個小時後,已是晚上八點多了,辦案警察來跟我商量:「主管扣押物品的警察喝醉了,來不了了,你能不能明天再來?」我大聲說:「那怎麼行?!這大夏天的,到處是蚊子。我從天亮就在這兒等,當中你們也不告訴我。現在這麼晚了,我去哪兒?你們警察怎麼能這麼辦事?」他說:「我也沒辦法。」於是我當著他的面撥通了110。聽了我的情況,對方答應馬上解決。就這樣,我堂堂正正的拿到了鑰匙,回了家。
幾天後,我又去了派出所,把公安部39號文件和新聞出版總署50號令的複印件當面交給了辦案警察。他想推脫不要,我鄭重的告訴他:「你必須收下,這是我提交的與本案有關的資料。這兩份文件就能證明我媳婦無罪,從我家裏抄走的東西也都不是違禁品。」於是,他老老實實收下了。
這時的公義論壇已經很完善,我按照論壇提供的模板填寫後,對涉案警察進行了控告,把控告信發到了國家、省、市、區的公、檢、法系統,同時也郵寄給了被控告的警察本人。之後,收到了幾個部門的電話反饋,有的表示同情,有的給出建議,無一例負面反饋。隨著案件的推進,我還向相關部門郵寄了《以案釋法申請書》、《變更強制措施申請書》、《不起訴申請書》和《排除非法證據申請書》等法律文書。
案子到了檢察院後,我找到辦案警察,告訴他:「按照法律,卷宗送達檢察院後,與案件有關的物品隨案移交,其餘的應該歸還家屬。」他告訴我說:「全部移交了,沒有返還的。」我向他索要扣押清單,他推三阻四的不給。為此我鄭重向他提出信息公開的要求──要求他向我提供派出所關於扣押物品處理的具體規定和相關流程。他嚇的夠嗆,說:「我們是合法辦案的,全程有錄像。」我告訴他:「我現在說的是信息公開,要求公開具體規定和辦事流程。」他實在沒辦法,幾天後把電腦、手機等電子產品還給了我。
非法判決下達後,說到了家中宣傳品非本人製作。於是,我拿著判決書到派出所,要求歸還與本案無關的物品。涉案警察還是拖著不辦,我就直接找到了區公安分局的信訪辦,正趕上局領導值班,聽了我的陳述,他表示對派出所的表現很不滿,答應不用我再跑,儘快解決。
誰知,接下來派出所還是繼續拖延不辦,我只能再次去了信訪辦。信訪辦主任聽完後說:「正好今天開會,你們那兒的所長和政保科的人都在,我把他們都叫來,面對面的把事兒說清,儘快解決了。」一會兒,所長和政保科的人都到了,政保科帶頭的是S。
S往對面一坐,上來就大聲喊:「法輪功的一切物品都是涉案物品!」然後問我:「聽見了嗎?」我剛說「聽見了」,他就說了一聲「那就行了」,轉身就走。我一下站起來,說:「站住!你告訴我,我家的打印機涉了甚麼案?」他尷尬的站在門口,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這時信訪辦主任過來說:「別急,你要甚麼寫下來,我給解決。」我一邊指出S的問題,一邊把《扣押清單》上的相關物品一一列出來,因為律師已經給了我清單。
幾天後,新接手的副所長L聯繫我,讓我們去拿東西,這時我妻子已經回家。到了派出所,我和妻子看了看滿地的東西,說:「還差平板電腦和播放器吧?」L說:「你那個平板電腦得告訴我密碼,確定裏邊乾淨才行。你說那個播放器是小收音機吧,那小卡上有『反宣品』內容,所以收音機可以給你,小卡不能給。」我說:「這樣吧,有爭議的下次再說,沒爭議的我們先拿走。」L高興的表示同意。
我又說:「可東西這麼多,當時是用警車拉來的,我們用手得搬到啥時候呀?要不你們用警車幫我們送一下吧!」L爽快的說了聲「沒問題」,然後又說:「別用那個帶警燈的了,太招搖,用那個公務車吧。」說完,他和幾個警察把東西一樣一樣的裝了滿滿一車。然後,L又跟車一直把東西送到我家。回去的時候,他討好的說:「大哥、大姐,今兒開車送東西可不是公務,這可是我個人的行為。」我們對他表示感謝。
因為我們堅持要大法書籍,Z所長接了手,把我們叫到一個單獨的屋子裏,低聲告訴我們:「你們給的文件我都看了,而且從網上、書上也查了資料,知道你們說的是真的,也是對的,也非常理解你們。但是,如果我擅自把法輪功的書給了你們,我這身衣服就別穿了(當不了警察了)。如果當時出警的時候我在場,也不會是這樣的結果。」
接著,他講了他在別的派出所時幫助法輪功學員的故事。談話中,明顯感覺他聽過真相,並接受真相。於是我們表示,為了不讓他為難,我們暫時先不提大法書的事,但不放棄。他很高興,說:「其它的電子產品還有沒發還的嗎?」我隨口說:「播放器的小卡還沒給。」他馬上說:「立即就辦。」
事後,有當地同修聽說了我家的經過,也正念強起來,要回了被非法扣押的三輪車。
上訴與申訴
妻子雖然回家了,但上訴還在進行中。向中院法官提交書面材料的同時,我申請做妻子的家屬辯護人,法官很痛快就同意了,並當場遞交了委託書。然後法官又問我們是否還需要法律援助律師,我們認識到這是接觸本地律師、向本地律師講真相的好機會,就說:「需要。」
回家後,我和妻子一起針對整個迫害過程中公、檢、法的所有違法之處,並結合一審非法判決書所有非法證據及結論,有理有據的寫了《上訴材料補充》。寫完後很快送到了中院,並利用每次與法官接觸的機會,儘量多向她講真相。
幾天後,接到一名女律師打來的電話,她說自己是D律師,受司法局委派做我妻子的法律援助律師,需要我簽一份委託書,並約我們去她律師事務所面談。到了約定時間,我們帶了公通字[2000]39號文件和第28期《國務院公報》來到了D律師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她很熱情,說她已經閱卷了。從卷宗看,確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並詢問我們的訴求是甚麼。妻子簡單講述了案件過程中公、檢、法種種違法之處,並告訴她我們要求二審公開開庭審理。D律師說她去和二審法官溝通一下,看看能不能達成。我又從法律角度講了信仰合法和迫害的違法,並給了她那兩份文件,請她多了解一下。
談話過程中,D律師表現的比較正義,對我們也很同情,我們也適當的誇獎和鼓勵她,最後我問她:「如果再有這類的情況,你願不願為法輪功學員做辯護律師?」她沒有正面回答,但言語中能聽出她是可以做的。
在此期間,妻子看到一篇文章《有感於一位常人郵遞萬封喊冤信 公安被迫撤案》。受此啟發,以請求二審公開開庭為由,寫了一封求助信。信中講述妻子遭受冤案的始末,公、檢、法各階段對妻子的違法對待,以及認定意見的違法、法律適用的錯誤,其中穿插了公通字[2000]39號文件內容和第28期《國務院公報》中新聞出版總署第50號令的內容,希望相關部門的領導能善用手中的權力,施以援手。
這封信寄往了所在區、市、省及中央各公、檢、法、黨委、政府機關等相關部門主要領導,陸陸續續寄出約有二百封。求助信寄出後,陸陸續續收到了12368訴訟服務熱線、來自省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短信,及省信訪局的短信五、六條,都表示會責成相關部門處理。
一個多月後,D律師告訴我說法官讓她交辯護詞,已經催了幾次,她有點擋不住了。我告訴她:「不能交,法官就是想不開庭,交了辯護詞,就直接結案了,我們就沒有辯護的機會了。」她很無奈,希望我跟法官溝通一下。
我和妻子商量:「看來中院是不想開庭。現在法官給律師施壓,畢竟是援助律師,她可能承受不住壓力,就可能不經過咱們同意就遞交辯護詞,這樣中院就不開庭直接結案了,以前咱們當地二審都是這樣草草結案的。為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咱們給中院遞交一份律師解聘書,這樣她就沒有代理咱們案件的資格了,法官也不會找她要辯護詞了。」我們很快寫了一份解除委託律師的書面聲明,交到了中院。法官也沒問解聘原因,只是問我們是不是還需要另外指派一名援助律師,我們自是欣然同意,因為這正是多接觸律師的好機會。過後D律師對我們這麼快解聘她表示不理解,我們告訴她:「是不希望你承受太大的壓力。」她也就理解了。
隨後,中院又指派了一位H律師。她第一次打電話時,上來就問上一個援助律師被解聘的原因,妻子說明了原委。她就說:「那你直接拒絕我吧,估計我也達不到你們的要求。」妻子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就同意了。
回家後,妻子和我說起,我說:「別直接就拒絕她,應該給她一個機會,最起碼咱們應該見面談談,她怎麼知道自己做不到呢?我給她打個電話再試試。」於是我撥通了電話,我說:「我們的要求其實也沒啥難做的,你們律師不是獨立辦案嗎?不是應該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嗎?你不交辯護詞,司法局又能把你怎麼樣呢?」她哈哈大笑,說:「也是,其實在司法局這邊也沒啥壓力不壓力的。不交辯護詞,我還省事了呢!」這樣我們約好去她律師事務所見面。
見面後,感覺H以前沒有接觸過法輪功,不了解,但是也不抵觸我們所講的。聊了大約兩個多小時,從我們這個具體案子到整體對法輪功的迫害;從兩高司法解釋的違法、違憲,到法院、檢察院被利用著錯誤的適用法律來迫害法輪功學員;從一九九九年前政府對法輪功的支持,到「七﹒二零」後的造謠抹黑;從「文革」、「六四」等歷次政治運動到迫害法輪功;從個人的冤案到整體社會民眾的人權、信仰、言論的缺失……
聊的過程中,也有其他人過來找她辦事,她迅速處理好後,依然回到我們的話題。雖然她很忙,但感覺她很願意聽我們講。最後H說:「非常佩服你們。」甚至笑著對我說:「大哥,你的水平都可以做專業律師了。」我也笑著回應說:「別的方面不敢說,在為法輪功辯護這方面,我敢說我不比專業律師差。」
最後H律師答應,不經我們同意,不會交辯護詞,並說再和中院溝通一下,爭取能開庭審理。我們給她留下了[2000]39號文件和新聞出版總署第50號令。我們起身離開時,她把我們送出律師事務所,說有事可以找她。後來本地再次出現同修被綁架到看守所,需要請律師單次會見時,我們給了家屬H律師的電話。家屬和同修找她時,她痛快的答應了,而且收費很低。
儘管我們很努力的想促成二審開庭,可還是沒有達成。歷經五個月後,法官給我打電話說:「二審不開庭了,書面審理。如果不交辯護詞,就視為放棄辯護權利。辯護人是否還是不交辯護詞?」我說:「是,我們不放棄要求公開開庭的權利。」
之後,妻子在網上投訴二審法官,依法追究其拒絕公開開庭審理的法律責任。收到二審裁定書後,妻子接到二審法官的電話,她說:「信訪部門收到了你的投訴,讓我跟你解釋。」妻子再次跟她說了我們認為應該開庭審理的理由,並且說書面審理、沒有辯護意見就結案是違法。二審法官辯解了幾句,最後說:「二審已經結束了,你申訴吧。」
此前,在當地認識的同修中還沒有聽說誰做過申訴,所以我們也不清楚申訴具體怎麼做,於是我們求助了公義論壇。公義論壇上同修在討論如何才能做好申訴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運用法律反迫害,目地是維護同修的合法權利,營救同修,但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形式講真相,救度世人。在這一點上,申訴比控告更具有優越性。控告狀的書寫格式非常嚴謹,無法展開講真相。而在申訴狀中,我們可以針對判決的違法之處展開講真相,法律上的、信仰上的,社會的普世價值、道德、正義、良知等等,都可以講。
於是我們明確了寫申訴書的基點,就是用申訴的形式揭露迫害、講清真相、證實大法、救度眾生。在申訴書中,先把公、檢、法每個階段所有違法犯罪的事實詳細的寫出來,然後對照相關法律,條理清晰的把公、檢、法公然違背法律、蓄意構陷的行為逐條列出,以此揭露公、檢、法披著法律的外衣踐踏法律、無所顧忌的迫害善良的合法公民,讓人看看到底誰在違法犯罪;並以法輪功不是×教展開講述法輪大法真相、洪傳全世界的盛況;中共打壓法輪功二十多年根本沒有法律依據,對法輪功學員迫害所依據的法律都是違法、違憲的,迫害的一切理由都是謊言,讓人們看清中共迫害法輪功的荒唐和邪惡。
最後,以妻子親身的修煉體會講述法輪大法的美好,澄清在迫害中中共製造的各種謊言,尤其是「天安門自焚」偽案,以「因果循環、善惡有報」的天理和現行的追責政策,勸善所有還在被裹挾著參與迫害法輪功的公、檢、法人員,要他們堅守良知,嚴格依據事實、法律,維護申訴人的合法權利,維護法律的神聖和尊嚴,從新審理此案,撤銷對申訴人的枉法判決和裁定,還申訴人以公平、公正。
我和妻子共同完稿後,以私信發給論壇專業同修修改把關。經論壇同修修改後打印,連同附件公通字[2000]39號文件和第28期《國務院公報》,通過中院申訴窗口遞交到中院。遞交前我們發願:讓每個看到申訴書的人都能了解真相,認清邪惡,不要再參與迫害,給自己選擇美好的未來。
申訴書投遞後,主管法官幾經輪換,看起來是拖長了時間,讓我們多跑了幾次。其實我們知道,這是讓更多的法官看到真相。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我們接到中院審監庭內勤的電話,通知一週後去中院開申訴聽證會。我們不清楚聽證會是咋回事,對方也說不清。我們問:「需要帶甚麼?」她說:「帶身份證就行。」我問:「家屬可以參加嗎?」她說:「可以。」
妻子上公義論壇向專業人士請教,論壇同修建議要熟悉自己的刑事申訴狀,並按照刑事案件一審開庭程序準備。論壇上一位開過聽證會的同修根據自己的經驗也給了一些寶貴的建議。我和妻子商量,我們每人準備一份辯護詞,獨立完成,互不依賴,確保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單獨面對都能把辯護意見表達的清楚完整。大概用了一週時間,我們各自寫了一份長達近十頁的辯護詞。在聽證會的前一天,我們才看到對方的辯護詞,非常神奇的是我們每個人都完整表達了無罪辯護的觀點,合在一起能夠互相補充,卻並不重複。
我們也把聽證會的消息告訴了本地同修,大家都非常支持配合。聽證會那天,很多同修去中院附近發正念,也有很多同修拿著身份證堂堂正正的入場旁聽。聽證會開始時我們才發現,這個申訴歷經一年多、輾轉三位法官,最後又回到了第一位法官那裏。也許是其他法官都通過申訴書看明白了,誰也不願接手這樣一個所謂的案子,不想再為這場迫害背黑鍋,所以互相推諉,以至一年多都沒有做任何處理,最後沒辦法,終點又回到了起點。
聽證會開始前,書記員問我的身份,我說:「是親友辯護人。」書記員問:「有委託書嗎?」我立即拿出來。因為有公義論壇同修的提醒,我們提前做好了準備。當時這個法庭還安排了另一個案子,竟然和我們是同一個時間。估計法官當時就想走走過場,幾句話把我們打發了事,所以書記員喊我們進去時,對另一波當事人說:「你們先等一會兒,一兒會招呼你們。」
法官沒有想到我們準備的那麼充份,聽證會開了一個多小時。妻子先陳述了案件過程及公、檢、法違法辦案之處,然後我宣讀了辯護詞。讀到講述法輪功基本真相及法輪大法洪傳全世界時,法官打斷說:「你們有紙質的文件?一會兒交給我們,有些細節部份就不要完整宣讀了。」我說:「好,這部份細節我就不讀了,我就讀結論。」我大聲宣讀:「所以,法輪功既非教,更不邪。從做人的角度看,從字典中再難找出比真、善、忍這三個字更好的標準來。將之視作邪教,無異於將聖者呼為盜賊。」法官低了頭。
當我讀到辯護詞中論述「司法解釋是在違法」的部份時,法官幾次打斷我,說:「你這是學術討論,我們不討論法律制定問題。」我立即明確告訴他:「這不是在做學術討論,這個冤案錯案的關鍵就是這個司法解釋。」法官沒有再說甚麼,於是我完整的讀完了整個辯護詞,並在最後強烈要求中院重啟再審程序。
感想
之一、修煉第一
師尊說:「個人修煉不能放鬆,無論你做甚麼事,講真相啊,或者是你做證實大法的項目,首先要把修好自己放在第一位,你做的那件事情才更加神聖,因為你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弟子在做證實法的事。」(《各地講法八》〈二零零七年紐約法會講法〉)
這麼多年走過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作為一個修煉者,不管有甚麼樣的技術、能力,如果心中沒有對師父對大法的正信,沒有清晰的法理,沒有強大的正念,甚麼也談不上。
有些說法,有些內容,即使知道該怎麼說,甚至能背誦下來,沒有心性做基礎,關鍵時候仍是大腦一片空白,說不出來;即使勉強說出來,也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只是一種輕飄飄的聲音,因為沒有修煉者的能量。
之二、無可顯示
師尊告訴我們:「大法弟子當前無論是集體證實法還是你個人的講真相,都是大法需要。正法需要,你就應該把它做好,沒有甚麼可說的。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也不要自己覺的和別人不一樣。你們都是一個粒子,在我的眼裏,誰都不比誰強,因為你們都是我同時撈起來的。(鼓掌)有的在這方面能力強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強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說我有這麼大本事啊,怎麼怎麼樣,那是法賦予你的啊!你達不到還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達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覺的你自己怎麼本事。有的學員想讓我看他的本事,其實我想,這都是我給的,不用看了。(《二零零三年元宵節講法》)
大法弟子都是好人,都是善良人,如果沒有這場迫害,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實在不需要了解這些枯燥的法律條文。而且有些法律詞彙和條款也確實不易看懂,不易理解。可是迫害發生了,而且邪惡在用整套法律系統參與迫害,已經持續了二、三十年。
於是願意學些法律知識,懂些法律知識,尤其是能在用法律反迫害中做些事的人,也就成了這方面有能力的人,也就免不了被同修推崇和讚揚。所以我提醒自己,有了一點點能力,千萬不能因此而生出甚麼歡喜和顯示來,其實也實在沒啥可顯示的。
之三、不被依賴
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能力不僅表現為會說、會寫,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敢說、敢寫。也就是說,對於很多同修來說,不單單是能力的問題,還涉及一個怕心的問題。本來能力就容易讓人產生依賴,而怕心更會加重這種依賴。
師父是讓我們每個弟子都修成,每個人都必須走出自己的路來,所以依賴和被依賴都是要不得的。顯示能力、大包大攬、幹事心強,不但是自己的修煉存在問題,而且也影響了同修的修煉,擋了別人的路,可謂害己害人。
師父說:「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關。」(《精進要旨三》〈走出死關〉)「可是有沒有怕心,卻是修煉者人神之分的見證,是修煉者與常人的區別,是修煉者一定要面對的,也是修煉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精進要旨三》〈學好法 去人心並不難〉)
去年鄰區的一位同修遭迫害,營救小組同修聯繫到我,我說:「這時應該給檢察院打電話,問問案子是否到了他們那兒。」可聯繫的同修說想讓我打這個電話。我思考了一下後,在信中回覆:「如果你們連這個都做不了,我就不參與了。」
事後,有同修對我表示不理解:「你為了不讓她們依賴,就忍心看著被迫害的同修不管?」我說:「如果我把這個電話打了,接下來所有出面對外的事都會成為我一個人的。她們不但做不了甚麼,而且在這一點上提高不上來,修煉不上來卻是我造成的。我們是修煉人,修煉才是第一位的。」
之四、關於請律師
在本地同修中,我是比較早接觸律師的,認識的律師也比較多。我個人感覺,「正義律師」這個群體的正義感正在越來越退化,就近兩年我的所見所聞,有些律師的表現就很是差強人意。當然,我們知道律師也面臨著壓力,而且他們並不修煉,只是職業行為。
而且作為看到、接觸到這些律師的不足表現的同修,也可能存在自己修煉方面的問題,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同時,也存在大法弟子對他們帶著人情式的推崇,談話中對他們那種黨文化式的恭維,也都是造成他們表現不盡如人意的原因。另外,全國各地都時有迫害發生,都在搶這點有限的資源。
所以很久以來,我就覺的應該充份利用給被迫害同修找律師的機會,通過打電話、發信息、發郵件或者面談等方式,大面積接觸當地律師,給當地律師講清真相。讓更多律師得救的同時,讓他們發揮作用,為大法弟子辯護,為自己選擇未來,改善當地的修煉環境。增加可用律師資源的同時,還存在收費低、聯繫方便、會見方便等諸多優勢。
在我妻子兩次遭迫害的過程中,我都在這樣做,而且沒有想像的那麼難。他們也是眾生,他們也在等著得救。而且因為他們有專業知識,從這一角度上說,他們更容易理解和認同大法弟子無罪。僅我妻子第二次被迫害期間,我聯繫的當地律師中,就有多達二十幾位律師願意為大法弟子做無罪辯護,而且最高收費只有一萬元,還有低於五千元的。
前些日子,我地又有一位同修遭非法抓捕,參與營救的同修來找我商量,我就把以上找律師的建議給了他。
另外,不知從甚麼時候起,我逐漸發現了一個現象:每當我要寫重要文字的時候,比如寫徵稿的時候,重感冒的表現總會突然而至,弄的我鼻涕一把淚一把的,干擾很大。等我寫完了,發出去了,這病業的表現也沒了。
我悟到:大法弟子的文章是有作用的,是能祛邪除惡的,是能救人的。所以,不管能不能發表,都要寫,都要認真完成。而且我由原來的強打精神,在承受痛苦中完成稿件,現在已經變為在主動正念除惡的同時寫稿了。
(全文結束,明慧網第二十二屆中國大陸法會來稿選登)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5/11/16/231337.html